譯 跋
詩就是在翻譯中丟失的東西���。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這句話道出了詩歌翻譯的困難之處����。但即便如此,仍有許許多多的詩人��、翻譯家以極大的熱情和毅力投入到詩歌翻譯的實踐之中���,為讀者提供了一首首精彩的譯作�。同樣����,詩就是在翻譯中所要找尋的東西�,我且固執(zhí)地這樣認為。翻譯藏族青年詩人那若的《殘垣》��,正是在丟失與找尋的二元悖論中走過每一個夜晚����。并非譯者的主觀感受如此,那若的詩歌歸根結(jié)底就是一種丟失與找尋的精神苦旅��。在丟失中找尋����,在找尋中丟失���,如此往返。詩人從世間形成歌謠的旋律開始����,在拉薩每一條街頭巷尾、每一處犄角旮旯���,始終如一等待著來世般的遙遠的拉薩耳環(huán)再次現(xiàn)世�。是的���,拉薩耳環(huán)��,只有妙音仙女才佩戴的拉薩耳環(huán)���,如今在鋼筋水泥鑄就的城市喧囂中早已銷聲匿跡,了無影蹤��。但詩人不相信眼前所顯現(xiàn)的景象��,更不相信自我所意識的現(xiàn)象���,以一種苦行僧式的心力�,甚或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依然彳亍前行,在前行中獨自吟唱關于拉薩耳環(huán)的歌謠�����,這歌謠源自遙遠的天界����,流在紛擾的塵世,凝于詩人的筆端�����,形成了張貼在拉薩夜晚的各種布告����。這是《殘垣》給我的初步印象�����。
《殘垣》入21世紀藏族作家書系第六輯�,于2014年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,是那若的第一部詩歌集��。《殘垣》收錄了作者自2000年以來創(chuàng)作的86首詩歌����,多半在《章恰爾》《崗尖梅朵》等藏區(qū)著名文學刊物發(fā)表,其中格律體10首���。在翻譯過程中���,除了一首格律體之外,其余均未翻譯���,而以近期創(chuàng)作的幾首自由體新詩代之�����。本人為那若詩集《殘垣》藏文版的責任編輯����,私下有同鄉(xiāng)之念����、好友之情,翻譯之責義不容辭�����。而本人也在翻譯過程中用盡渾身解數(shù),細致謹慎�,數(shù)易其稿,力求譯詩信���、達����、雅���。愿望雖如此美好���,但對于詩歌翻譯來說,達成則非易事���,尤其像我這樣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翻譯新手來說���,其難度不言自明�。更何況那若的詩歌中引用了很多佛學術(shù)語、經(jīng)典語句��,甚至涉及《四部醫(yī)典》等藏族醫(yī)學著作。以上種種��,無形中給翻譯工作帶來了諸多困難與障礙�,冥冥之中印證了弗羅斯特的那句話。不管怎樣����,我盡量用自己的真心彌補那些翻譯中丟失的東西,又盡量用自己的實意挽回翻譯中找尋的東西�����。
在具體實踐中�,本人處處注意翻譯的準確性與藝術(shù)性的平衡,同時�,在兩者之間取舍選擇中,更加注重表達的準確性���,因而有意放任了很多藏化句法�、文法的出現(xiàn)��。我在想:這不僅對變相體會《殘垣》中隱藏著的深厚的民族文化����、獨特的生命體驗��、優(yōu)雅的語言文字有所幫助����,而且將逼出漢語詩歌寫作的新火花�。
毋庸諱言,在我們這一代介于70后和80后之間的無代人中間����,那若的詩歌創(chuàng)作一開始就顯得與眾不同。早在上大學期間���,他的詩歌創(chuàng)作帶有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穩(wěn)重�����、大方大氣的特質(zhì)��。后來�����,大學碩士畢業(yè)���,他去往西藏大學任教,我當時就草率地認定他會向著學者�、教授的路子發(fā)展而不再堅守詩歌陣地,藏族文壇從此將會失去一位可塑性極強的詩人��。后來的實踐證明我的判斷完全錯誤��。在拉薩生活�、工作幾年后,他以一個新的筆名(那若)依稀出現(xiàn)在《章恰爾》《崗尖梅朵》等期刊上�����。一種熟悉且陌生的感覺自內(nèi)心油然而生�����,熟悉的是他的音容笑貌依舊如故�,陌生的是他的詩風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(zhuǎn)變。其中緣由無從知曉�,也不想探個究竟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:如此地理跟文化意義上的接近藏族中心地帶�,對我們西藏之外的藏族學子們有極大的身心觸動,而這種看不見��、摸不著、道不明的觸動����,儼然使他的詩風漸趨含蓄且飽滿、內(nèi)斂且奔放�����,猶如含苞待放的花朵����,恰似閨中待嫁的少女。
縱觀那若2000年以來創(chuàng)作的詩歌��,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讀者品味:意象之獨創(chuàng)性���,情感之向善性���,語言之精辟性,在當下青年詩歌寫作者中�����,可謂獨樹一幟�,少有望其項背者����。比如說他的詩歌意象:以時間等抽象的事物在詩歌中的形象化處理����,以耳環(huán)等具象的事物在詩歌中的朦朧化應用���,都達到得心應手���、爐火純青的地步,其閱讀效果與欣賞價值都具有很高的藝術(shù)水準���,這些由詩人匠心營造���、烙有非常私人化特質(zhì)的意象,不同于以往藏族詩歌中固定生成的如太陽�����、蓮花等傳統(tǒng)意象�,為那若詩歌意境之幽遠空靈起到不可小覷的作用,個中奧妙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��。比如說他的詩歌情感無論是對一個不起眼的老舊蟲穴,還是對一個風塵仆仆的陌路人�����,他心生精益��,筆起敬畏����。如果詩人不具有強烈的向善發(fā)心,這些字句將會顯得矯揉造作����、蒼白無力,正如詩人自己所言:在西藏�����,本人試圖將編制虛構(gòu)和想象���,沿襲并傳承這生長于大愛之上的敘事傳統(tǒng)��。還有����,那若的詩歌語言是千錘百煉后的結(jié)晶,是磨礱淬勵后的正果����,短小且不失精悍,簡潔又不乏詩意��。另外���,作為當下性的詩歌經(jīng)驗,他卻反其道而行����,大量引用佛學術(shù)語、經(jīng)典語句�,且如此應用之巧妙,讓人拍手稱快�,贊不絕口,使詩歌在閱讀中有了返璞歸真�、古色古香的外在美感和內(nèi)在享受。
像《念住》這樣包括標題在內(nèi)帶有濃厚佛教意蘊的詩歌���,看似冗長拖沓���,前后毫無關聯(lián)���,置讀者于閱讀障礙與陌生化的雙重境地。但仔細咀嚼����、品味,讀者不難會發(fā)現(xiàn)詩人頗具匠心的用意和大膽前衛(wèi)的手法�。全篇由63個單句以并列的形式組成,每一個單句獨自成一個章節(jié)����,而每一個章節(jié),又有其不失整體感的立意和想象空間��。最后一行單句�����,是整首詩的詩眼��,有了這個詩眼����,再讀前面62行單句,你會有一種答疑解惑、豁然開朗的感覺���,這種反向環(huán)扣或障眼的手法���,其結(jié)構(gòu)之巧、寓意之妙��,實在百看不厭�����,余味深長���。作為后記,限于篇幅�����,在此不再一一贅述���。希望以上提點能起到觀其全貌�、窺其全豹的作用���。
最后����,感謝中國作家協(xié)會、青海省作家協(xié)會����,是他們給予我這樣一次難得的機會,使《殘垣》漢譯版得以付梓出版����,與藏文讀者以外的更多的詩歌愛好者進行文本意義上的潛在交流。感謝作家出版社編輯史佳麗�����、李亞梓女士��,恩師蔡煌道杰先生�����,是他們的不吝指正與修改����,為拙譯增色,熠熠生輝。我相信�����,這將會使《殘垣》漢譯版無愧與原作者和廣大讀者見面�����。愿一切吉祥�。
是為跋。
譯者于古青塘城雪石齋
2017年11月28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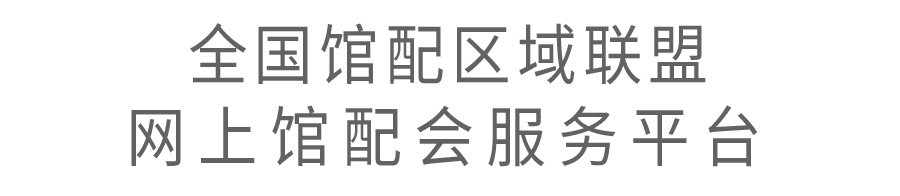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