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筆留下那些會疼的時間
葉延濱
讀榆木的詩稿���,感受到一種久違的樸實而真誠的情感��,讓我從眾多的詩稿中�����,將其選出推薦給其他編委��。我不認識這位生活在礦井的詩人�����,此前也沒有讀過他的詩����,但他的詩作得到多數(shù)編委的認同���,脫穎而出���,成為本屆叢書中唯一入選的詩集,這是大家對一位真正深扎在大地深處詩人的認可����。當我讀到他的《礦工》:“除了黑乎乎的煤。我們/
還能從地下深處再掏出什么/可是���,埋在地下深處的/除了煤�,還有活著的我們”��;钪奈覀儯@一行詩使讀者對詩人的關(guān)注與對底層勞動者的關(guān)注合而為一����,我們能從榆木有活力并且有骨感的詩行中,領(lǐng)略一個當代勞動者內(nèi)心的豐厚與堅實��。
詩人是光明的歌唱者�,從古到今的詩人永恒的主題是愛,是光明�,是對自由的向往。這就讓詩歌有了向善向上的力量����,引領(lǐng)生活在污濁混沌之中的人們向往著光明和自由;讓處于長夜迷霧中的眼睛仰望星空�����。在榆木的詩中��,生活在礦井中的人們���,黑暗與光明���,不是一種詞匯����,而是對生活最重要的判斷:“在地下���,我從不敢大聲喊你們的名字/
我害怕這黑乎乎的巷道悄悄地記住你們//因為我的親人�����,就是被這黑暗給扯住的/至今���,還沒有回家”。這首《名字》將礦工內(nèi)心最深刻的感受���,用平實的語言呈現(xiàn),驚心動魄���,入骨三分��。當下詩壇不缺少有才華的詩人�,但缺少對現(xiàn)實能如此真實地把握���。不是血淋淋就深刻��,也不是展示丑陋就先鋒�����。榆木的這幾行詩�,是人生的寫照,是命運的呼喊�����,更是生命發(fā)自靈魂深處的回響���。當一個詩人身體貼近大地���,他的詩行也有大地給予的力量。
某些流行的寫作潮流���,對引領(lǐng)讀者向上的精神元素����,好像避之不及,不說理想�,不談追求,不向往明天�,把玩自己那點無奈與無聊,變?yōu)橐环N寫作時尚���。理論家們不會忘記說以人民為中心�,然而只有當詩人真正是人民的一分子并且與其共命運的時候��,那些光彩的詞匯才會因人民真實理解而獲得生命力�。詩人榆木的《理想》一詩寫道:“他說:還清房貸,我就不干煤礦了/他說:存上十萬塊錢�,我就不干煤礦了/他說:給孩子攢上結(jié)婚錢,我就不干煤礦了/……/他們都這樣說����,一心想著離開煤礦/十多年過去了。在六百米深的地下�,他們/依然被黑乎乎的巷道緊緊地咬住”。這就是那些最平凡的礦工的理想��,高尚嗎��?遠大嗎��?不�,真實而沉重。這也是人民的理想�����,是對抗黑暗��,是堅持現(xiàn)實����,是不得已而拼死的努力。當我們習慣于展示光鮮成就的時候����,別忘了理想大道上的這些鋪路石!我們每個人都承受著現(xiàn)實的擠壓�,我們都經(jīng)歷過光明黑暗的交替,詩人榆木把這個普世的命運共性��,以礦井與礦工的獨特方式呈現(xiàn)���,用生命體驗書寫我與我們���,我們與世界的關(guān)系���,從而以小我與一個礦工群體的大我,合而為一�����,成為其精神代言者:“我們的身體里是不是藏了太多的黑暗��。所以/才把人間僅剩給我們的一點光明帶入地下交換/我們的生命里是不是放不下太多的光明�����。所以/一盞礦燈在地下便給了我們足夠多的亮光生存/有時候�����,我們也在想:什么時候離開煤礦啊/可我們清楚地知道��,脫下這身工作服/我們就養(yǎng)活不起這個家//我們的這輩子是不是向每一塊煤借來的�。所以/今生的時光我們都在身不由己地償還直到身骨顫抖/我們的親人是不是也欠給光明一次黑暗。所以/他們的生前就已經(jīng)把掛念托付到地下沒日沒夜/有時候��,我也很高興:孩子能叫爸爸了/可離開家的時間久了����,再回去/他又得重新學習‘爸爸’這個詞語//我們的日子究竟是不是一塊塊煤堆積來的。所以/當我們把一座大山挖空的時候�,為何我們所剩時日已經(jīng)不多/我們的暮年是不是真的不需要煤的留戀,然而/當我們風燭殘年還要把一顆像煤一樣黑的藥/嗑進身體里……”(引自《一個煤礦工人的感
想》)讀到榆木的這首詩����,我體會到,當黑色的煤開始燃燒����,它就告別了黑暗成為光明的使者;當一個礦工開始思考��,他就不僅是黑色礦井中的勞作者而是點燃人心的詩人����。中國曾出現(xiàn)過一些優(yōu)秀的礦工詩人,他們歌唱底層的勞動者和他們從事的事業(yè)���,榆木加入了這個隊列�,同時他又超越了礦工歌手的身份�,成為深刻揭示礦工命運的思想者,這是他努力完成的使命�,也是為當下詩壇開掘的新礦坑道。
特別讓我感到驚喜的是詩人不僅對底層礦工群體有深切的理解��,同時作為一個受過現(xiàn)代教育的礦工,在深處地底的黑暗坑道中���,內(nèi)心光明而透徹�����,身處黑暗坑道�,思如明麗星空��。這是時代給予詩人的精神力量�,也是詩人為這個時代呈現(xiàn)的真正的詩意棲居。詩人以《余生清白》這首詩作為詩集
名��,我以為在這首詩中抒發(fā)了詩人對生活的期許和熱愛:“我獨愛著樹葉縫合的風��。門墩上/我獨愛著螞蟻奔跑的孤寂����。幾叢雜草長進院子/我獨愛著它們幽深時的模樣。幸好我來時帶著雨//雨水里有一個春天���。有我倔強的本性/有我一動身就來臨的夜晚������;璋档臒艄饫�/有我關(guān)心的女人提鞋蹚過河流//河流的水可涼過腳面����。我愛這冰涼的河水/是多年以后����,我們回到地下的體溫”��。這是一幅充滿溫情而又略為寂寥的畫面��,人性的光燭讓平凡世界的野草落葉��,有了時間的刻度和目光的撫愛�。有了這樣的詩作,作為一個礦山生活的詩人榆木��,再次證明��,在這個互聯(lián)互通的時代����,職業(yè)的界限在消退,詩人或許是不同人群找到共同聯(lián)系的信使�。好的詩人永遠是相同的����,高尚�����、博愛���、真誠�����、善良�����、悲憫���,這些精神的元素,使詩人成為大多數(shù)人的朋友���。那些缺少這些精神元素的人����,縱有才華,也經(jīng)不起歲月和塵世的搓揉��,成為一閃而逝的流螢���。榆木的詩作能讓我們感受一個好詩人的悲憫情懷��,在不經(jīng)意的詩行中�����,滲透了體察、理解和愛:“落在晾衣繩上的燕子瞅瞅母親/她正坐在大門口的石頭上/磕著鞋里的土�����。假裝沒有看到燕子/我知道���,那是她在害怕/如果����,視線撞在一起/她擔心會驚走一個嘮嗑的人”����。讀到這樣的詩句��,我們也為孤獨的母親而心口疼痛����。詩人正是用筆����,將那些溫暖的時間、流淚的時間�、疼痛的時間,一點點地留下來���,正如《會疼的時間》寫道:“我勾勒的局部�,一只螞蟻從石頭高處摔下來/如果看得足夠仔細�����。那只螞蟻并沒有掉在地上/美好的想象有時候是一種傷害����。我不知道它該落在哪里/一棵草,一片葉子��。或者河流��,和云彩/
落在哪里都覺得會摔疼西山的子民����。所以/我決定,就把它留在時間以外�����。順應(yīng)天命/總有一天���,它會弄疼時間”�����。說得好,順應(yīng)天命�����,保持一個詩人對萬物的愛��,化萬物于大愛����,大愛之詩聯(lián)通萬物���。希望詩人珍惜從地底坑道中捧回的那顆赤子之心,不斷在詩藝上精進努力����,相信能有更多更優(yōu)秀的作品
問世。
是為序��。
2019年歲末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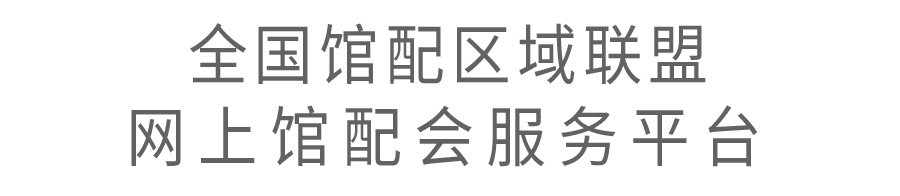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