敘目
第一章 《經(jīng)言》九篇
第二章 《外言》八篇
第三章 《內(nèi)言》九篇
第四章 《短語(yǔ)》十八篇
第五章 《區(qū)言》五篇
第六章 《雜篇》十三篇
第七章 《管子解》五篇
第八章 《輕重》十九篇
附錄一 戰(zhàn)國(guó)前無(wú)私家著作說(shuō)
附錄二 古代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中之本農(nóng)末商學(xué)說(shuō)
附錄三 古代政治學(xué)中之皇、帝�、王、霸
敘目
甲書雜乙丙之言���,則甲之思想學(xué)說(shuō)混����;周書羼秦漢之語(yǔ)����,則周之學(xué)術(shù)系統(tǒng)亂;辯偽之學(xué)所以不容已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f(shuō)�,按之學(xué)術(shù)思想雖未必盡驗(yàn),而后人之作���,亦未必皆遜于前��;古人之言����,亦未必盡善。辯偽者���,每貴遠(yuǎn)���,崇古卑今,一若閑圣護(hù)道者然�����。真古人者���,奉為珍寶�,舁于九天�;偽于后者,視如糞壤�����,拋于九淵�����。胡應(yīng)麟為《四部正訛》曰:“唐宋以還�����,贗書代作�����,作者口傳��,大方之家���,第以揮之一笑���。乃衒奇之夫,往往驟揭而深信之����;至或點(diǎn),廁賢撰�����,矯前哲,溺后流�����,厥系非渺淺也�����!”至康有為著《新學(xué)偽經(jīng)考》�����,更變本加厲����,謂:“不量綿薄,摧廓偽說(shuō)����,犁庭掃穴,魑魅奔逸���,雺散陰豁�����,日黋星呀��;冀以起亡經(jīng)��,翼圣制��,其于孔氏之道����,庶幾御侮云爾����。”流風(fēng)所被���,成為去取定于真?zhèn)��,是非判于古今���,辯偽之書出����,而古籍幾無(wú)可讀焉��!
古人,斯誠(chéng)卑矣���。然周秦諸子����,靡不托古改制��,茍其言之成理���,持之有故����,皆宜保存�����;惟疏通明辯��,使還作主���,而不贗偽古人���,亂學(xué)術(shù)之系統(tǒng)已耳�����。如《列子》出晉人�����,非列御寇作已漸成定讞。晉人之書�,傳者絕鮮,據(jù)此以究戰(zhàn)國(guó)學(xué)術(shù)固妄�����;據(jù)此以究晉人學(xué)術(shù)���,則絕好材料����,不得以其非列御寇作���,而卑棄不一顧��。故余以為與其辯真?zhèn)����,必益以考年代�,始于古人����,有裨于今后之學(xué)術(shù)界也。惟史料之書用在史實(shí)����,后人向壁虛造,自全無(wú)價(jià)值�����。如《竹書紀(jì)年》出汲冢�,真?zhèn)喂貌徽摚癖救羌弛Vf�����,淆混史實(shí)�,錯(cuò)亂年代,誠(chéng)宜析辯而雜燒之�。即言理之書,若《文子》之襲《淮南》,慎懋賞本《慎子》之衲百家(余別有《慎懋賞本〈慎子〉辯偽》����,載《燕京學(xué)報(bào)》第六期),割裂剿同��,毫無(wú)詮發(fā)���,原書可讀�,何須乎此���?亦應(yīng)疏通證明,無(wú)使濫竽著作之林����,而耗學(xué)子披。
考年代與辯真?zhèn)尾煌恨q真?zhèn)��,跡追依偽,擯斥不使廁于學(xué)術(shù)界���,義主破壞�����;考年代���,稽考作書時(shí)期��,以還學(xué)術(shù)史上之時(shí)代價(jià)值�����,義主建設(shè)����?寄甏���,則真?zhèn)我嘁蛑@���;辯真?zhèn)������,而年代或仍不得定�?/span>
吾國(guó)為文明古國(guó)���,學(xué)術(shù)思想,發(fā)達(dá)最早��,書籍浩繁,幾為全球冠��;而詳贍有系統(tǒng)����、有組織之學(xué)術(shù)史,今尚闕焉�����。區(qū)區(qū)小子�,未敢多讓,思竭綿薄���,從事于上古一部����。而各書真?zhèn)������,前人雖略有考訂��;至其年代�,則論及者鮮。朱紫并收���,一依舊題作者為敘���,則虛偽不實(shí),無(wú)史之價(jià)值��;且學(xué)術(shù)系統(tǒng)���,亦茫不可理����。去偽存真��,則有價(jià)值之材料����,坐視廢棄,故不得不先為考年代之學(xué)�。海內(nèi)賢達(dá),有聞之而興起者乎����?各以性之�����,力之所長(zhǎng)�����,擇年代未定之書�����,分別研討���,則書定年代,而光明燦爛之學(xué)術(shù)史��,可企足而待矣��。
《管子》非管仲書�,前人多能言之�����,多能信之���。傅子曰:“《管子》之書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�。”(王應(yīng)麟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引�,劉恕《通鑒外紀(jì)》引。)蘇轍曰:“至戰(zhàn)國(guó)之際��,諸之著書����,因管子之說(shuō)而增益之。其廢情任法遠(yuǎn)于仁義者�����,多申韓之言�����,非管子之正也�������!保ā豆攀贰す荜塘袀鳌罚┤~石林曰:“其間頗多與《鬼谷子》相亂。管子自序其事���,亦泛濫不切��,疑皆戰(zhàn)國(guó)策士相附益����。”(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引�����。按《鬼谷子》晚出書��,鈔《管子》�,非《管子》鈔《鬼谷子》。)葉適曰:“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筆����,亦非一時(shí)之書,莫知誰(shuí)所為�����。以其言毛嬙����、西施、吳王好劍推之�����,當(dāng)是春秋末年���。又‘持滿定傾�,不為人客’等���,亦種蠡所遵用也�����!保ā端募罚┲熳釉唬骸啊豆茏印分畷s����。管業(yè)著者�����,未必曾著書��。如《弟子職》之篇��,全似《曲禮》,他篇有似《老》《莊》���;又有說(shuō)得太卑��,真是小意智處���,不應(yīng)管仲如此之陋。內(nèi)政分鄉(xiāng)之制����,《國(guó)語(yǔ)》載之卻詳��!庇衷唬骸啊豆茏印贩枪苤偎V佼�(dāng)時(shí)任齊國(guó)之政���,又有三歸之溺�����,決不是閑工夫著書底人���;著書者,是不見(jiàn)用之人也。其書想只是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人收拾仲當(dāng)時(shí)行事言語(yǔ)之類著之��,并附以他書�������!保úⅰ吨熳诱Z(yǔ)錄》)黃震曰:“《管子》書不知誰(shuí)所集�,乃龐雜重復(fù),似不出一人之手�������!保ā饵S震文集·管仲論》)朱長(zhǎng)春曰:“大氐周衰道拙,至雄國(guó)而祖霸賤王大甚���,天下有口���,游談長(zhǎng)短之士,都用社稷����。管仲為大宗,因以其說(shuō)系而祔之,以干時(shí)王���,獵世資�����。田齊之君����,亦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為最勝��,夸一世而存雄��。故其書雜者��,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泛談�����,而半乃韓非李斯輩襲商君以黨管氏���,遂以借名行者也��。故其書:有春秋之文�����,有戰(zhàn)國(guó)之文����,有秦先周末之文,其體立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!视抟浴读凶印窌姵������,與《莊子·雜篇》����,與《管子》���,皆多偽不可信����。”(《管子序》)至如宋濂《諸子辨》���、姚際恒《古今偽書考》���、紀(jì)昀等《四庫(kù)提要》,皆有疏辯之言�,以其皆書,不一一征引�。惟既“非一人之筆,一時(shí)之書”��。而各篇作于某家����,成于某時(shí),無(wú)人究論��,故治周秦兩漢學(xué)術(shù)者���,終于躊躕卻顧�,而割而棄之也��。
考《漢志》���,《管子》八十六篇�����,今亡者才十篇��,在先秦諸子����,裒為巨帙,遠(yuǎn)非他書可及�。《心術(shù)》《白心》���,詮釋道體,《老》《莊》之書����,未能遠(yuǎn)過(guò);《法法》《明法》�,究論法理,《韓非·定法》《難勢(shì)》�,未敢多讓;《牧民》《形勢(shì)》《正世》《治國(guó)》�����,多政治之言;《輕重》諸篇又為理財(cái)之語(yǔ)�;陰陽(yáng)則有《宙合》《侈靡》《四時(shí)》《五行》;用兵則有《七法》《兵法》《制分》�����;地理則有《地員》��;《弟子職》言禮�;《水地》言醫(yī);其他諸篇�,亦皆率有孤詣。各家學(xué)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保存最夥����,詮發(fā)甚精,誠(chéng)戰(zhàn)國(guó)秦漢學(xué)術(shù)之寶藏也��。寶藏在前而不知用��,不以大可惜哉!不揣梼昧��,按之本篇�,稽之先秦兩漢各家之書,參以前人論辯之言���,為《管子探源》八章�,《附錄》三篇�����。橫分某篇為某家(如儒家���、陰陽(yáng)家��,政治思想家),縱分某篇屬某時(shí)�����。信以傳信�,疑以傳疑。然后治學(xué)術(shù)史者���,可按時(shí)編入�����;治各種學(xué)術(shù)者�����,亦得有所參驗(yàn)����。寶藏啟而戰(zhàn)國(guó)秦漢之學(xué)術(shù),乃益彪炳而偉大矣�����。...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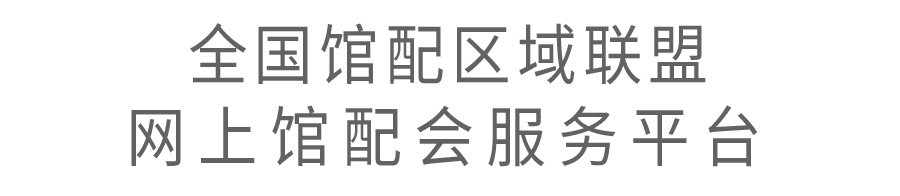
 書單推薦
書單推薦 新書推薦
新書推薦